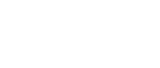北京的煤场都去哪了?
他的不少诗,就以三家哲学为讽刺对象。
仿照一句常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,也可以说:大众传媒面前人人平等。西方中世纪后期转入封建化,而中国中世纪后期却没有发生这种转变,依然顽固地保持着皇权独大的专制帝国制度,缺乏皇权之外的某种独立的、可以与之抗衡的社会力量(例如独立的教权、贵族权力、市民权力),其中的缘由尚待探讨,但这对于后来历史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:其现代化的过程异常艰难。

平等者,‘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是也。[69]康有为:《论语注》,见《康有为全集》第六集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393页。[37]《诗经》: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所以,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福柯(Michel Foucault),在反思启蒙的同时,并不是抛弃启蒙承诺,而是寻求一种新的、更彻底的启蒙,即更彻底的个体精神,亦即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,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,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,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、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。我曾说过,民粹主义(populism)其实并非什么主义,而是一种社会情绪,因而可以与任何主义结合,包括与极权主义结合。
[60]黄宗羲:《原君》,《明夷待访录》,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笛卡儿哲学是抽象的形而上学,现在我们有了具体物的原则。其实,在这三项中,大一统与郡县制,都未必是儒家的专利,反而有可能是法家的东西。
[107] 今天的中国大陆,真的就像西汉文景时代转向汉武时代了吗?也许是的,中国大陆的思想世界,也许正如他们所说,大陆新儒家开始与自由主义、社会主义鼎足而三,各自为未来中国设计路径。78、姚中秋,〈秩序底定与史学再造——围绕钱穆的讨论〉,载《文化 纵横》2015年10月号,页124。100、陈明语,〈专题: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〉,《天府新论》2016年第 2期,页4。比如,康晓光就曾经给未来中国勾画新的蓝图,他说这个新蓝图的灵魂,还是我们中国儒家的思想,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,所以,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‘儒教国,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‘儒化。
36、关于这一点,参见韦伯,《支配的类型》,见《韦伯选集》III(康乐中译本,台北:允晨文化公司,1985);鄂兰(大陆译汉娜·阿伦特),《极权主义》(蔡英文中译本,台北:联经出版公司,1982,1992)。为什么是回到康有为,而不是章太炎或张之洞?是因为章太炎只是小中华方案,康有为才是大中华 方案。

在这一点上,我们注意到1989年事件之后仅仅几个月,蒋庆就在台湾的《鹅湖》月刊发表长达三万五千字的《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》,这篇被视为大陆新儒家宣言的论文,其实,也可以看到大陆新儒家试图在政治上不认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,在思想上另寻立场和起点的意图。[43]可是,非常吊诡的是,从学理上说,这个所谓合法性必须有不言而喻的来源,只有这个来源具有权威,它才能成为合法性依据。关于中国大陆所谓新左派与大陆新儒学关系的问题,这里不能详说,还需要有专门的论文来详细讨论。并且说,如果把儒教作为国教,则需要具备三个系统,一是教义系统(经学与教育),二是意识形态系统(解决合法性的王官学),三是社会系统(风俗与礼乐)。
在这里,仍需简略回顾两岸新儒家几十年来的演变过程。但是,也有新儒家学者反驳陈明说,如果顾忌到儒家思想中隐含的汉族中心主义,反对按照公羊学的说法讲礼乐中国,那么,就丢掉儒家最有价值的部分,而只满足于追求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目标,我觉得有点儿削足适履。就像俗话说的,皇帝轮流做,明年到我家,谁是天生的统治者呢?就连古代皇帝,也要通过历史(论述前朝弊政和本朝德政)、封禅(祭天祀地祈求上天护佑)、符瑞(发现象征天意的祥瑞符玺)、德运(比附五德始终),甚至神话(皇帝的出身传说)等,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,那么需要追问的是,儒家设计的这个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‘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,它本身的合法性来源究竟在哪里?它会不会就是传统时代那个披着儒家外衣的君主专制体制?[44] 也许,他们不需要这样追问,作为信仰者,信仰总是不需也不能质疑的,但是作为思想者,思想却是随时要追问的。46、王懋竑,《朱熹年谱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98)卷一,页2。
[24]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,他们一方面依据传统中国的华夷之辩,一方面又加上了西方的丛林法则,提出一个很有颠覆性的观点:过去的新儒家之所以不得不接受普世价值,是因为这些普世价值来自西方,为什么呢?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强大,因而它成为世界不能不遵循的原则。随后发言的一位学者进一步对康有为的国教论,作出让人很难理解的解释,第一,孔教不是儒教,第二,孔教不一定是 宗教,第三,孔教天然是国教。

二是在儒学之士中选拔贤能,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的考试才能获得从政资格,就如同当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,各级党政干部也要把儒家经典当作学习的主要内容[75],在现代环境中重建中国政教治理模式[76]。今天的中国,还需要重建内外上下、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。
81、康晓光,〈我为什么主张儒化〉,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,页 165。77、蒋庆,〈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〉,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,页42-43。37、即林毓生所说的普遍王权(Universal Kingship),参见林毓生,《思想与人物》(台北:联经出版公司,1983),页149。这并不是他随口所说,在其〈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〉中又 说夏商周『三代』即有儒教,因儒教是一文明体,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,可能在汉武帝时代并没有流传,也没有真正被采纳,所以有人指出天人三策流传民间可能始于昭宣时期,而《史记》的董仲舒传也没有提及。[108]在这样的情势下,他们或许会忘记,儒家历史上真正的政治批判者与思想阐发者,恰恰应当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,也就是应当务正学以言,无曲学以阿世[109]。
35、刘泽华曾经批评新儒家以及倾心于新儒家的学者,多半绕开儒术与帝王的关系来论述儒家的主旨(《中国政治思想通史(综论卷)》 (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4),页134。见任重主编,《儒学复兴:继绝与再生》(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2012),页11-13。
中国国性不复存,中国沦为非驴非马之国矣,也就是说,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,所以,他呼吁归来乎,儒生。这里新儒家 大体上是指海外新儒家,可是现在大陆新儒家已经不再绕开这一点,干脆直接提政治儒学,把儒家与皇权直接连接起来了。
这些从口号、观念到制度的论述和设想,改变了现代以来新儒家——1949年以后是海外新儒家——的基本理念和追求方向,使得大陆新儒家与自由主义、社会主义等一道,成为中国大陆思想文化论争,甚至是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。其实,这种用理论和术语包装起来绕着弯讲的话,不妨直截了当地说出来,就是今天的中国,需要一个象征宇宙意志的君主,无论是虚君还是实君,他既代表政治上的权威,也代表神圣的意志,还代表儒家的真理。
见唐文明,〈政治儒学复兴的正当性问题〉,载范瑞平等编,《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》(上海:华东师大出版社,2012),页94-95;更奇怪的是,原本学历史的姚中秋(秋风)居然说周代封建基本架构是自由人透过书面契约所建立的君臣关系,双方都是自由的,可以解除君臣契约,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,页280;又说董仲舒与汉武帝时代,就已经形成了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,说董仲舒策动了汉武帝时代的宪政主义革命。一、从思想立场上分道扬镳:严分夷夏的大陆新儒学 毋庸置疑,大陆新儒学是1980年代之后受到海外新儒家的启发,才逐渐滋生起来的,过去,他们曾把海外新儒家称作自己的接引者,所以,无论在思想资源还是学术脉络上,应当说他们都是一脉相承,也是同气相求的。按照他们的设想,儒化社会之步骤如下:一是最关键的,是把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,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国学课[73],恢复小学和中学的读经科,在大学恢复经学科,作为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[74]。66、参看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,页175-179。
那么,怎么能够不乱呢?他们说,康有为已经想到了外力冲击,少数族群主政,地域广阔,族群复杂这些因素[50],同时也想到了由于从清代中国到现代中国,疆域、族群那么庞大和复杂,因此,缺乏一个国家认同的基础便无法凝聚人心。[51]特别是,康有为在现代国际巨变的环境中,先是主张保全大清帝国而提倡君主立宪,后来中华民国建立,共和大趋势似乎不可逆转,他就主张虚君共和。
[62] 大陆新儒家五大重镇共著书名中国必须再儒化,就是在传达他们的这一理想和抱负。【作者说明:这是2017年3月在哈佛大学召开的一次当代中国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。
所以他们才会认为,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不再中国的原因,蒋庆曾激动地说,悲乎。49、 《何为普世?谁之价值?》,页72。
[89]但是作为儒家政治意识形态推手象征的董仲舒,始终鼓励或刺激着后世儒家学者对于政治和制度的热情。一个自称儒家的学者说,如果我们把外来的价值普世化并且尊奉它,那么,就意味着我们是自我夷狄化。还有一位学者说,海外新儒家的问题,就是把儒家理想仅仅放在内圣的层面来考虑,而且认同西方那套自由、民主的价值。[105]因此,他们觉得现在大陆新儒家登场,就应当像董仲舒一样,等待汉武帝垂询,与汉武帝形成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,完成所谓革命或更化[106],并且在郡县制的基础上,兴起文教,塑造儒家士大夫这样一个社会领导阶层。
由此来完成儒家‘王官学的现代复位。他们绝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的一个流派。
为什么?因为当时中国周边都是些小国,打也打不过中国,骂也骂不过中国,这样,中国的价值就成了普世价值。62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,页162。
说得比较理智和客气的,如制度儒学的提倡者干春松,他在《制度儒学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)前言中说在某种程度上,『制度儒学』可以看做是与『心性儒学』相对的儒家的另一面。63、也许,康晓光、王达三和蒋庆的论述,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设计方案?比较早的有康晓光《文化民族主义论纲》,他提出四项措 施:一,儒学教育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,二国家支持儒教, 将儒教定为国教,三,儒教进入日常生活,成为全民性宗教, 四,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。